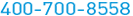陈琬:凡寻找美的,必寻见美
发布时间:2016年07月25日
倘若要盘点20世纪以来纽约最自由的灵魂,比尔·坎宁安(Bill Cunningham)必然位列前三页内,即便他毕生从业于最受商业控制的道场:时尚。如何检认一个人是否自由?夫子自道,多有粉墨矫饰;也不能相信作息时间表,因为那常只看出一个人的百无聊赖。要看的是人对“美”的定义。在自由的心里,美就是站在我们庸常的人生中,目送俏姑娘蕾梅黛丝(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人物)升天,每天至少一次。
比尔的蕾梅黛丝,他称之为 Stunner 的那种人,在第五大道和第75街的十字路口,每日层出叠现,化身为年龄、性别、种族各异的过客。从1966年至临终,在他最喜欢的这个角落,比尔看见全世界向他涌来。他们身上的衣服,正切切向他述说无数“我是谁?”的证辞。整整半个世纪,比尔为此着迷不止,他承认自己从来只看到了衣服,以及衣服如何被穿出来,而自动过滤掉了衣服主人们住的房子、开的车子、手中的权柄或话筒。
1978年有件事后来传遍了纽约文艺圈:一个穿着海狸皮大衣的女人跃然入目,比尔念念不忘大衣式样如何惊艳,情不自禁跟拍了一路,放下相机发现整条街的行人也追视着这个女人。他想,纽约人真识宝。直到发表这套照片的时候,才被编辑发现:这个女人是葛利泰·嘉宝啊!
在自我世界中独断专行,是艺术家伟大的本能,是他们护卫创造力火种的金钟罩,非如此不可。相机常常被比喻成武器,大多数仰赖媒体的摄影师,先不论本性如何,得把攻击性这件职业装穿在外面。偏偏比尔的独断专行,又表现得毫无攻击性——作为摄影师,他实在太腼腆了,所以他为自己选定了别的原则,并贯彻终生:终生清贫,由此不屈从于任何牵制。
惯见纸醉金迷的纽约后来还真容下了他这样的图纹(pattern):他的工作服,一式穿了一辈子,是环卫工人的蓝布制服,20美元一件,可以随便扔洗衣机;2美元的一次性雨衣,破了洞用胶布补上。无论到哪里——中央公园的周日集会,或下城的慈善晚会,比尔永远只骑单车。在纽约,他骑坏或骑丢了近30辆单车。他在卡耐基音乐厅楼上租了小小的工作室,一住半个世纪。房间被隔为上下两层,好存放他所有的底片。睡哪里?海绵床垫,四角用牛奶箱子支起。衣柜?所有的衣服,两三个衣架就挂完了。只用楼道的公用洗手间,而且从来不需要厨房,楼下最便宜的馆子,咖啡、香肠、煎蛋、芝士,一套基本早餐才三美元,他每日的物质所需已经满足了。这个世界越来越难相信人可以如此简单。
谁能收买比尔呢?《纽约时报》每周给他共计三个半版的完全自主权,分作两个栏目——街头时尚摄影 On the Street 和城中夜场报道 Evening Hours。如此厚遇,也直到1994年,他骑车被撞,为了医疗保险救命,才同意接受《纽约时报》收编为正式雇员。此外,连一盒巧克力这样的小礼物,也不能侵入他的世界。他每夜接连要探访拍摄几场上流社交圈的晚宴,从来先草草吃点快餐,到现场连一杯水都不会喝。他不是去拍名人的,因为颁奖礼上的明星们不会也不敢自己挑衣服,所以并没有“穿出他们自己真实的模样”。他只指认那些能让他眼前一亮的人,撞见纽约街头的西班牙国王夫妇,提个塑料袋溜达,他觉得这混搭真有趣。比尔是时装周的贵客,但他不相信秀场是时尚的全部。是他先看到了街头时尚如何自下而上动撼设计界;他是那个隐形人,为纽约录下衣香鬂影正浓,城中望族垂垂老去,他的老邻居、摄影师同行、安迪·沃霍的缪斯 Editta Sherman 在月光下的曼哈顿公寓里灭了灯,盈盈跳起《天鹅湖》,都是哪一年的旧事了。
比尔1929年出生在一个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家庭,精神世界在慈父严母间两极摆荡。19岁从哈佛退学,跑到纽约当裁缝店学徒,斟酌路人的衣着成痴,有时觉得他们哪里穿错了,就默默在心里为他们改出该有的样子。踏入时尚领地伊始,他就警醒自己不要落入富贵的诱捕。自朝鲜战场退役后,他创立了自己的礼帽品牌 William J.,没敢用全名,因为父母会因为他与女性时尚走得近而难堪。其间他经历了一生最窘迫的日子:给整栋楼的房东搞卫生以弥补房租,在药房打零工,近中午时得放下手头的帽子出门送外卖,晚上帮人做会计活,好有更多的零钱购买材料。这么穷过一次,比尔获得了终身的免疫力:自由比钱,贵重太多。
也许知情者也陆续不在人世了,比尔的爱情指向,无人知晓。早在《纽约时报》能在正文中使用“gay”这个词之前很久,比尔在他的夜场专栏里多次报道关注艾滋病的慈善活动。64岁那年的独立日,他的街拍专栏出了最具性别意识的一辑:《穿裙子的男人们》。比尔从不沾染政治,但这并未妨碍其所秉持之自由,由己及人。
2016年6月25日,比尔辞世,享年87岁。他没有自己的家庭,而人人都为他着上盛装。他未自称艺术家,可被他拍进照片里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成了艺术家。他全心贡献在时尚领域,人却始终置身事外,从而玉成纽约最自由的灵魂。于是我们可以认定,自由即:凡寻找美的,必寻见美。
*文章来源:财新文化
原刊于《财新周刊》2016年28期
转载已获作者授权
*通讯员:闫雯
*责任编辑:贾荣荣
比尔的蕾梅黛丝,他称之为 Stunner 的那种人,在第五大道和第75街的十字路口,每日层出叠现,化身为年龄、性别、种族各异的过客。从1966年至临终,在他最喜欢的这个角落,比尔看见全世界向他涌来。他们身上的衣服,正切切向他述说无数“我是谁?”的证辞。整整半个世纪,比尔为此着迷不止,他承认自己从来只看到了衣服,以及衣服如何被穿出来,而自动过滤掉了衣服主人们住的房子、开的车子、手中的权柄或话筒。
1978年有件事后来传遍了纽约文艺圈:一个穿着海狸皮大衣的女人跃然入目,比尔念念不忘大衣式样如何惊艳,情不自禁跟拍了一路,放下相机发现整条街的行人也追视着这个女人。他想,纽约人真识宝。直到发表这套照片的时候,才被编辑发现:这个女人是葛利泰·嘉宝啊!
在自我世界中独断专行,是艺术家伟大的本能,是他们护卫创造力火种的金钟罩,非如此不可。相机常常被比喻成武器,大多数仰赖媒体的摄影师,先不论本性如何,得把攻击性这件职业装穿在外面。偏偏比尔的独断专行,又表现得毫无攻击性——作为摄影师,他实在太腼腆了,所以他为自己选定了别的原则,并贯彻终生:终生清贫,由此不屈从于任何牵制。
惯见纸醉金迷的纽约后来还真容下了他这样的图纹(pattern):他的工作服,一式穿了一辈子,是环卫工人的蓝布制服,20美元一件,可以随便扔洗衣机;2美元的一次性雨衣,破了洞用胶布补上。无论到哪里——中央公园的周日集会,或下城的慈善晚会,比尔永远只骑单车。在纽约,他骑坏或骑丢了近30辆单车。他在卡耐基音乐厅楼上租了小小的工作室,一住半个世纪。房间被隔为上下两层,好存放他所有的底片。睡哪里?海绵床垫,四角用牛奶箱子支起。衣柜?所有的衣服,两三个衣架就挂完了。只用楼道的公用洗手间,而且从来不需要厨房,楼下最便宜的馆子,咖啡、香肠、煎蛋、芝士,一套基本早餐才三美元,他每日的物质所需已经满足了。这个世界越来越难相信人可以如此简单。
谁能收买比尔呢?《纽约时报》每周给他共计三个半版的完全自主权,分作两个栏目——街头时尚摄影 On the Street 和城中夜场报道 Evening Hours。如此厚遇,也直到1994年,他骑车被撞,为了医疗保险救命,才同意接受《纽约时报》收编为正式雇员。此外,连一盒巧克力这样的小礼物,也不能侵入他的世界。他每夜接连要探访拍摄几场上流社交圈的晚宴,从来先草草吃点快餐,到现场连一杯水都不会喝。他不是去拍名人的,因为颁奖礼上的明星们不会也不敢自己挑衣服,所以并没有“穿出他们自己真实的模样”。他只指认那些能让他眼前一亮的人,撞见纽约街头的西班牙国王夫妇,提个塑料袋溜达,他觉得这混搭真有趣。比尔是时装周的贵客,但他不相信秀场是时尚的全部。是他先看到了街头时尚如何自下而上动撼设计界;他是那个隐形人,为纽约录下衣香鬂影正浓,城中望族垂垂老去,他的老邻居、摄影师同行、安迪·沃霍的缪斯 Editta Sherman 在月光下的曼哈顿公寓里灭了灯,盈盈跳起《天鹅湖》,都是哪一年的旧事了。
比尔1929年出生在一个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家庭,精神世界在慈父严母间两极摆荡。19岁从哈佛退学,跑到纽约当裁缝店学徒,斟酌路人的衣着成痴,有时觉得他们哪里穿错了,就默默在心里为他们改出该有的样子。踏入时尚领地伊始,他就警醒自己不要落入富贵的诱捕。自朝鲜战场退役后,他创立了自己的礼帽品牌 William J.,没敢用全名,因为父母会因为他与女性时尚走得近而难堪。其间他经历了一生最窘迫的日子:给整栋楼的房东搞卫生以弥补房租,在药房打零工,近中午时得放下手头的帽子出门送外卖,晚上帮人做会计活,好有更多的零钱购买材料。这么穷过一次,比尔获得了终身的免疫力:自由比钱,贵重太多。
也许知情者也陆续不在人世了,比尔的爱情指向,无人知晓。早在《纽约时报》能在正文中使用“gay”这个词之前很久,比尔在他的夜场专栏里多次报道关注艾滋病的慈善活动。64岁那年的独立日,他的街拍专栏出了最具性别意识的一辑:《穿裙子的男人们》。比尔从不沾染政治,但这并未妨碍其所秉持之自由,由己及人。
2016年6月25日,比尔辞世,享年87岁。他没有自己的家庭,而人人都为他着上盛装。他未自称艺术家,可被他拍进照片里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成了艺术家。他全心贡献在时尚领域,人却始终置身事外,从而玉成纽约最自由的灵魂。于是我们可以认定,自由即:凡寻找美的,必寻见美。
*文章来源:财新文化
原刊于《财新周刊》2016年28期
转载已获作者授权
*通讯员:闫雯
*责任编辑:贾荣荣
最新新闻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