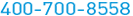朱睿:公益如何创新
发布时间:2015年11月18日
去年最令人瞩目的新闻事件之一,当属9月19日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功挂牌。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在财富方面创造了两个纪录:一是马云迅速接过中国内地首富的桂冠;另一个是,马云的公益信托基金将超过20亿美元的规模,这一数字将马云送入世界知名慈善家之列。马云有关公益的一举一动,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美国19世纪末最知名的企业家和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这句话经常被人挂在嘴边。
和卡内基同时代、全球最富有的人约翰·洛克菲勒,也曾因为自己捐钱的速度无法赶上收入增长的速度而倍感沮丧。洛克菲勒一直以私人捐赠为乐趣,涉及慈善的事大都亲力亲为。但是他面对的各种请求压得他苦不堪言。曾经仅仅一艘轮船就从欧洲给他带来5000多封乞求救助的信件。一个月之内,他曾经收到多达5万封信件。他在1886年时说:“我不会随便给人一点点好处,除非我能完全保证这是我花这笔钱的最好方式。”这句话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听上去都有点刺耳,但是话糙理不糙,隐藏在这句话背后的真相是:草率花钱是慈善的业余水平。
从无到有,中国的公益事业正在步入一个令人向往的成长期。但是,中国的公益事业最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一场理念更新的头脑风暴。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公益?做公益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公益是否应该考虑效率?在公益介入的过程中,受助者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从根本上厘清这些疑问,走出公益的误区,我们最需要的是理念上的创新。
从范畴来看,公益的内容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从做法来说,公益应该讲求效率并且应该用商业的模式来做公益。从结果上说,公益应该强调受助者的参与和责任。否则,这样的公益是有害的。
公益需要的是爱心和智慧的结合,缺一则不称其为真正的公益。爱心点燃了公益的火把,智慧可以让这个火把持续地燃烧。爱心让我们在公益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智慧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快。
公益范畴比想象的要丰富
要说清楚公益的范畴,最具启发意义的人物便是美国19世纪末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从某种意义上说,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史,是美国慈善历史的一个缩影。
芝加哥大学是美国最富盛名的大学之一,迄今已有89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此工作或学习。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这所大学是由洛克菲勒于1890年捐资创办的。在建校五周年的庆祝活动上,洛克菲勒在一个巨型帐篷里对现场的1500多人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明智的投资。”
和很多超级富豪一样,洛克菲勒也是花了几年的时间,才学会用一种系统、科学而又同他的财富规模相称的方式捐钱。对这位商界巨子而言,最没有想象力的花钱方式就是把钱直接交给别人,而不是用来探索人类苦难的根源。“如果钱不是施舍给乞丐,而是用来研究产生乞丐的根源,那么,一些更有深度、广度和价值的事情就会得以实现。”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与绝大多数慈善家不同的是,洛克菲勒的公益行为更多地致力于促进知识创造,超越感恩和回报这个层面,超越个人色彩这个维度,其影响也更为深远。
19世纪后期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一样,许多富豪热衷于向学校和博物馆捐款。比如,靠铁路发家的约翰·霍普金斯和利兰·斯坦福,先后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学,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匹兹堡的卡内基大学和遍布世界的卡内基图书馆,让卡内基这位钢铁大王的名字流传至今。但是,洛克菲勒没有让自己的名字挂在芝加哥大学的墙上。他不允许大学里的任何建筑带有他的名字,洛克菲勒纪念教堂也是在他故去之后才命名的。
洛克菲勒不赞成分散地搞捐赠,而是慷慨资助那些在研究上能产生广泛影响的机构。洛克菲勒基金会是美国医学研究、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的主要赞助者。洛克菲勒本人也成为历史上向医学界捐助最多的人。在他一生所捐赠的5.3亿美元中,有4.5亿美元直接或者间接地投向了医学。在推动美国医学水平上升至世界领先地位的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受益者,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中国医学委员会,1921年建立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向中国捐赠的资金仅次于美国。
2000年,比尔·盖茨和夫人梅林达创办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该基金会赞助的一个重点领域是医学,有关研究计划体现了软件工程师追求细节的特点:比如为孕妇注射疫苗以降低新生儿死亡率,研发高收益、抗病虫害的杂交香蕉品种等等。
盖茨基金会的“探索大挑战”,自2008年启动以来,已经为全球60多个国家超过1070个获奖者提供了超过1亿美元的资助。在过去六年中,共有16份来自中国的创新提案获奖。该项目致力于资助那些可以解决全球健康与发展瓶颈问题的创新项目。
纵观慈善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慈善的内容正在从低级过渡到高级、从原始进化到文明、从简单演变到复杂,从一开始的接济和救助变得更加宽泛和丰富。中国的慈善步伐也丝毫不落后。比如,马云的公益基金将致力于污染治理和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每个季度,阿里巴巴的高管们会专门拿出一天的时间来讨论水和树的保护。在中国香港,亿万富豪香港富商陈启宗的家族慈善基金“晨兴基金会”于今年9月向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赠3.5亿美元,创下了哈佛378年校史上金额最大的单笔捐赠。
但是,这还不是公益的全部定义。公益的范畴比我们的理解要宽泛得多。只要是社会问题,都属于公益的范畴。比如洛克菲勒家族还做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捐资修建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提高人们的审美趣味,让人们看到美、欣赏美、传播美,这是更高层次的公益。
借鉴商业模式做公益
罗宾汉基金会是目前纽约最大的、致力于与贫困做斗争的公益机构。董事会承诺将每一位捐助者的捐款100%地投放给资助项目。去年,罗宾汉基金会向纽约市超过210个对抗贫困的项目投放1320万美元。
在罗宾汉资助的住房项目中,有92%的受助者再也没有回到过去的庇护所。罗宾汉资助的教育项目将通过GED考试(美国高中毕业证书)的几率增加75%。罗宾汉的职场训练项目比其他机构的效率高出一倍。同其他城市的项目相比,参加罗宾汉项目的人可以获得更高的薪资和工作留用率。一般的公益机构,每年的公益晚会平均可以筹集300万-500万美元的善款,但是去年,罗宾汉基金会仅一个晚上便筹集高达5700万美元的善款,前来捧场的不乏政界和演艺界的名流要人。
为什么这家公益基金会能如此大放异彩?为什么它能保持如此骄人的公益纪录?
答案是这家基金会有一套特有的项目评估方法:绝对货币化(RelentlessMonetization,简称RM)。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学术化,这与罗宾汉基金会的创始人及主要资助者的专业背景有关系。他们大都来自对冲基金和金融机构,许多人是受过专业训练、沉迷于数学模型的“宽客”(Quants)。
1988年创立之初,罗宾汉基金会就誓言将“投资原则”应用于公益事业。董事会成员们坚持的理念是,将他们投资于公益的每一分钱,都像他们投资于对冲基金一样有效。董事会引入了一位经济学家、毕业于MIT的迈克尔·温斯坦(Michael Weinstein)出任基金会的首席项目官(Chief Program Officer)。迈克尔开发出这套严格的评估体系RM,目的是帮助资助人做出最划算、最高明的公益决定。
把投资原则和公益弄到一块儿,那怎么可能?!这是我在商学院讲授公益课的时候,遇到的最常见的反诘。的确如此,将程式化、数量化和结果导向的投资战略,与讲求爱心、讲求奉献的公益诉求结合在一起,猛然一听,有点让人抓狂。即便在罗宾汉基金会,这一努力一开始也遇到了重重阻力。但是这些阻力并没有让他们知难而退。原因很简单,罗宾汉基金会的创始人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有过一个惨痛的、为期五年的教训。
保罗是美国著名的投资人。26岁时,他创立了私人资产管理公司和对冲基金都铎投资公司。在2014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他以43亿美元的身价位居全美第108位和全球的第345位。
上大学的时候,保罗还是拳击冠军。20多岁的时候,他曾经申请就读哈佛商学院,虽然拿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却最终没有成行。因为在打点好了行李准备出发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我现在拥有的这些本事是商学院不可能教给我的”。
在美国投资界,保罗是个有传奇经历的操盘手。在中国,他的投资理念和骄人战绩也为不少投资人津津乐道。保罗和妻子曾经资助一所小学的一个班级,两人在这些孩子身上花费了不少金钱、时间和精力。比如,每年寒暑假他们都带这个班的学生参加夏令营和冬令营。下雪天,他们还会给孩子们送去免费的晚餐。论金钱,夫妇俩的投入不可谓不多,论爱心,两人的付出也不可谓不真。五年之后,当这个班级的毕业成绩摆在两人面前的时候,他们无语了:这个班级并不比其他没有人领养的班级更出色。
这让保罗反思:我有如此丰富的经验和能力,为什么我做公益的效果反而不明显呢?
保罗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做公益跟做企业一样,公益需要的不仅仅是一颗火热的心,公益更需要专业的技能和实业化的管理。这个理念也成为罗宾汉基金会的安身立命之本。
对所有已经投身或者即将投身公益事业的人们来说,有一点务必牢记:我们身处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慈善家或者资助者不可能资助每一个行善事的项目,他们必须做出取舍。
怎样取舍呢?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应该选择那些把每一分钱都用到极致的项目。否则,钱就被白白浪费了。对那些苦苦等待救助的社会需求来说,这种浪费是一种无法原谅的错误。
公益机构最大的特点是非营利性。非营利意味着赔钱,但是赔钱并不必然等同于浪费和低效率。换句话说,正是因为非营利,才更应该有效率,更应该让公益的每一分钱都获得最高的社会回报。
要让给予变得有聪明,要让非营利机构变得有效率,要让慈善变得更公平,其实,我们有现成的方法可资借鉴,这种方法恰恰来自于已经在几百年的演化过程中变得极为成熟的营利性机构。
对营利性机构而言,衡量其成功与否有一个天然的尺度:投资回报率(return oninvestment,ROI)。而困扰公益机构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没有一个可以将不同的公益效果进行测算和比较的天然尺度。
比如,举个环保方面的例子,是应该把钱放在建设生态厕所上还是用于治理雾霾?在教育方面,是应该把钱用来资助在广大农村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还是帮助贫困地区的学生改善饮食标准,是捐建乡村小学图书室还是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脑瘫儿童轮椅?罗宾汉基金会的评估方法RM,就是找到了一个类似“投资回报率”的指标,即公益回报与投资成本之比。这种测量公益效果的方法让不同公益项目之间的比较不仅变得可行而且清晰有据。
RM的核心思想是将不可类比的公益回报货币化。这种方法最独特的贡献是将货币价值赋予公益效果,从而将对公益效果的评价转化为对其货币价值的比较。不管你是捐助者、非营利机构、政府官员、立法部门、政策专家或者任何从事公益项目的人,这种方法都可以提供一种可靠、透明的答案。
每年,大约有5%-10%的公益机构在第二年得不到罗宾汉基金会的资助。并不是因为这些机构做的事情不重要、不伟大,并不是说他们爱心不够多,而是因为这些项目没有达到预期设计的目标。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做法和慈善的本质背道而驰,而且非常残忍。但是对捐资人来说,这是最有效率的公益,是最公平的做法,是社会效益最大化的选择。
在商学院,每当我讲完保罗的故事,课堂里都非常安静。我想那些志在投身中国公益事业的同学们已经明白,他们心中的问题不再是是否去做,而是如何将每一个项目的评估公式化和数量化。毫无疑问,这个做法确实是有难度,但不是不可为。我坚信用商业模式做公益,一定是中国公益事业未来的方向。如果这套创新的理念和方法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国的公益事业就不算成熟和理性。
让受助者独立
在《洛克菲勒传》中,洛克菲勒说过一句话让我深受震动:如果不能让受益者独立,慈善是有害的(Charity is injurious unless it helps the recipient to become independent of it)。这个理念,对投身公益事业的人士来说,应该贯穿公益行动的始终。
也就是说,金钱的额度和爱心的真诚固然令人尊敬,但是我们救助受助者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他们独立起来,不再需要我们的帮助,这才是公益最大的成功。如果救助者离开我们的帮助还不能独立,这样的公益不仅有害,对救助者来说,也是一种失败。
斯坦福发展中经济体创新研究院(The Stanford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Economies,简称SEED)的做法就与众不同,他们通过创新的方式来做公益,让受助者变得独立。实际上,创新不应该是企业竞争的专利,社会组织也应该通过创新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去年6月在非洲加纳,30多位当地的创业者接受了SEED的培训。他们的企业规模在15万美元左右,但仍有增长的潜力。这些培训旨在帮助当地企业家战胜非常迫切的挑战,比如如何吸引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学习的内容包括硅谷的热门课程:设计思维、供应链管理等等。培训的讲师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校友和志愿者。讲师们和企业家一道展开工作,帮助他们获得融资,甚至细致到招募合适的团队。这些企业慢慢地越做越好,变得更具竞争力之后,企业家可以去扶植当地其他的缺乏经验的创业者。
SEED的想法是,在与贫困斗争的过程中,增加就业机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私人企业在创造和扩大就业这方面扮演了非常高效的角色。通过孵化创业企业、帮助有一定规模的当地企业更具规模,可以让更多的人摆脱贫困,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位于美国硅谷的斯坦福大学,一直被视为新创企业的孵化器,对硅谷的兴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将这方面的经验运用于全球贫困落后地区的私人企业,就显得格外有意义。真正的社会公益不应该是简简单单地投一笔钱,而应该通过搭建一个平台、形成一个机制,以最少的投入实现最大的效益。有趣的是,SEED的赞助人、斯坦福校友罗伯特·金是百度的早期投资人,这笔投资给他带来丰厚的回报。
让爱心归爱心,让公益归公益,让效率成为最大的公平。要真正做到和西方一样成熟,中国的公益事业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让我们从起点开始。
*文章来源:年代智库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美国19世纪末最知名的企业家和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这句话经常被人挂在嘴边。
和卡内基同时代、全球最富有的人约翰·洛克菲勒,也曾因为自己捐钱的速度无法赶上收入增长的速度而倍感沮丧。洛克菲勒一直以私人捐赠为乐趣,涉及慈善的事大都亲力亲为。但是他面对的各种请求压得他苦不堪言。曾经仅仅一艘轮船就从欧洲给他带来5000多封乞求救助的信件。一个月之内,他曾经收到多达5万封信件。他在1886年时说:“我不会随便给人一点点好处,除非我能完全保证这是我花这笔钱的最好方式。”这句话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听上去都有点刺耳,但是话糙理不糙,隐藏在这句话背后的真相是:草率花钱是慈善的业余水平。
从无到有,中国的公益事业正在步入一个令人向往的成长期。但是,中国的公益事业最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一场理念更新的头脑风暴。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公益?做公益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公益是否应该考虑效率?在公益介入的过程中,受助者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从根本上厘清这些疑问,走出公益的误区,我们最需要的是理念上的创新。
从范畴来看,公益的内容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从做法来说,公益应该讲求效率并且应该用商业的模式来做公益。从结果上说,公益应该强调受助者的参与和责任。否则,这样的公益是有害的。
公益需要的是爱心和智慧的结合,缺一则不称其为真正的公益。爱心点燃了公益的火把,智慧可以让这个火把持续地燃烧。爱心让我们在公益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智慧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快。
公益范畴比想象的要丰富
要说清楚公益的范畴,最具启发意义的人物便是美国19世纪末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从某种意义上说,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史,是美国慈善历史的一个缩影。
芝加哥大学是美国最富盛名的大学之一,迄今已有89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此工作或学习。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这所大学是由洛克菲勒于1890年捐资创办的。在建校五周年的庆祝活动上,洛克菲勒在一个巨型帐篷里对现场的1500多人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明智的投资。”
和很多超级富豪一样,洛克菲勒也是花了几年的时间,才学会用一种系统、科学而又同他的财富规模相称的方式捐钱。对这位商界巨子而言,最没有想象力的花钱方式就是把钱直接交给别人,而不是用来探索人类苦难的根源。“如果钱不是施舍给乞丐,而是用来研究产生乞丐的根源,那么,一些更有深度、广度和价值的事情就会得以实现。”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与绝大多数慈善家不同的是,洛克菲勒的公益行为更多地致力于促进知识创造,超越感恩和回报这个层面,超越个人色彩这个维度,其影响也更为深远。
19世纪后期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一样,许多富豪热衷于向学校和博物馆捐款。比如,靠铁路发家的约翰·霍普金斯和利兰·斯坦福,先后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学,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匹兹堡的卡内基大学和遍布世界的卡内基图书馆,让卡内基这位钢铁大王的名字流传至今。但是,洛克菲勒没有让自己的名字挂在芝加哥大学的墙上。他不允许大学里的任何建筑带有他的名字,洛克菲勒纪念教堂也是在他故去之后才命名的。
洛克菲勒不赞成分散地搞捐赠,而是慷慨资助那些在研究上能产生广泛影响的机构。洛克菲勒基金会是美国医学研究、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的主要赞助者。洛克菲勒本人也成为历史上向医学界捐助最多的人。在他一生所捐赠的5.3亿美元中,有4.5亿美元直接或者间接地投向了医学。在推动美国医学水平上升至世界领先地位的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受益者,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中国医学委员会,1921年建立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向中国捐赠的资金仅次于美国。
2000年,比尔·盖茨和夫人梅林达创办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该基金会赞助的一个重点领域是医学,有关研究计划体现了软件工程师追求细节的特点:比如为孕妇注射疫苗以降低新生儿死亡率,研发高收益、抗病虫害的杂交香蕉品种等等。
盖茨基金会的“探索大挑战”,自2008年启动以来,已经为全球60多个国家超过1070个获奖者提供了超过1亿美元的资助。在过去六年中,共有16份来自中国的创新提案获奖。该项目致力于资助那些可以解决全球健康与发展瓶颈问题的创新项目。
纵观慈善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慈善的内容正在从低级过渡到高级、从原始进化到文明、从简单演变到复杂,从一开始的接济和救助变得更加宽泛和丰富。中国的慈善步伐也丝毫不落后。比如,马云的公益基金将致力于污染治理和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每个季度,阿里巴巴的高管们会专门拿出一天的时间来讨论水和树的保护。在中国香港,亿万富豪香港富商陈启宗的家族慈善基金“晨兴基金会”于今年9月向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赠3.5亿美元,创下了哈佛378年校史上金额最大的单笔捐赠。
但是,这还不是公益的全部定义。公益的范畴比我们的理解要宽泛得多。只要是社会问题,都属于公益的范畴。比如洛克菲勒家族还做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捐资修建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提高人们的审美趣味,让人们看到美、欣赏美、传播美,这是更高层次的公益。
借鉴商业模式做公益
罗宾汉基金会是目前纽约最大的、致力于与贫困做斗争的公益机构。董事会承诺将每一位捐助者的捐款100%地投放给资助项目。去年,罗宾汉基金会向纽约市超过210个对抗贫困的项目投放1320万美元。
在罗宾汉资助的住房项目中,有92%的受助者再也没有回到过去的庇护所。罗宾汉资助的教育项目将通过GED考试(美国高中毕业证书)的几率增加75%。罗宾汉的职场训练项目比其他机构的效率高出一倍。同其他城市的项目相比,参加罗宾汉项目的人可以获得更高的薪资和工作留用率。一般的公益机构,每年的公益晚会平均可以筹集300万-500万美元的善款,但是去年,罗宾汉基金会仅一个晚上便筹集高达5700万美元的善款,前来捧场的不乏政界和演艺界的名流要人。
为什么这家公益基金会能如此大放异彩?为什么它能保持如此骄人的公益纪录?
答案是这家基金会有一套特有的项目评估方法:绝对货币化(RelentlessMonetization,简称RM)。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学术化,这与罗宾汉基金会的创始人及主要资助者的专业背景有关系。他们大都来自对冲基金和金融机构,许多人是受过专业训练、沉迷于数学模型的“宽客”(Quants)。
1988年创立之初,罗宾汉基金会就誓言将“投资原则”应用于公益事业。董事会成员们坚持的理念是,将他们投资于公益的每一分钱,都像他们投资于对冲基金一样有效。董事会引入了一位经济学家、毕业于MIT的迈克尔·温斯坦(Michael Weinstein)出任基金会的首席项目官(Chief Program Officer)。迈克尔开发出这套严格的评估体系RM,目的是帮助资助人做出最划算、最高明的公益决定。
把投资原则和公益弄到一块儿,那怎么可能?!这是我在商学院讲授公益课的时候,遇到的最常见的反诘。的确如此,将程式化、数量化和结果导向的投资战略,与讲求爱心、讲求奉献的公益诉求结合在一起,猛然一听,有点让人抓狂。即便在罗宾汉基金会,这一努力一开始也遇到了重重阻力。但是这些阻力并没有让他们知难而退。原因很简单,罗宾汉基金会的创始人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有过一个惨痛的、为期五年的教训。
保罗是美国著名的投资人。26岁时,他创立了私人资产管理公司和对冲基金都铎投资公司。在2014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他以43亿美元的身价位居全美第108位和全球的第345位。
上大学的时候,保罗还是拳击冠军。20多岁的时候,他曾经申请就读哈佛商学院,虽然拿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却最终没有成行。因为在打点好了行李准备出发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我现在拥有的这些本事是商学院不可能教给我的”。
在美国投资界,保罗是个有传奇经历的操盘手。在中国,他的投资理念和骄人战绩也为不少投资人津津乐道。保罗和妻子曾经资助一所小学的一个班级,两人在这些孩子身上花费了不少金钱、时间和精力。比如,每年寒暑假他们都带这个班的学生参加夏令营和冬令营。下雪天,他们还会给孩子们送去免费的晚餐。论金钱,夫妇俩的投入不可谓不多,论爱心,两人的付出也不可谓不真。五年之后,当这个班级的毕业成绩摆在两人面前的时候,他们无语了:这个班级并不比其他没有人领养的班级更出色。
这让保罗反思:我有如此丰富的经验和能力,为什么我做公益的效果反而不明显呢?
保罗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做公益跟做企业一样,公益需要的不仅仅是一颗火热的心,公益更需要专业的技能和实业化的管理。这个理念也成为罗宾汉基金会的安身立命之本。
对所有已经投身或者即将投身公益事业的人们来说,有一点务必牢记:我们身处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慈善家或者资助者不可能资助每一个行善事的项目,他们必须做出取舍。
怎样取舍呢?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应该选择那些把每一分钱都用到极致的项目。否则,钱就被白白浪费了。对那些苦苦等待救助的社会需求来说,这种浪费是一种无法原谅的错误。
公益机构最大的特点是非营利性。非营利意味着赔钱,但是赔钱并不必然等同于浪费和低效率。换句话说,正是因为非营利,才更应该有效率,更应该让公益的每一分钱都获得最高的社会回报。
要让给予变得有聪明,要让非营利机构变得有效率,要让慈善变得更公平,其实,我们有现成的方法可资借鉴,这种方法恰恰来自于已经在几百年的演化过程中变得极为成熟的营利性机构。
对营利性机构而言,衡量其成功与否有一个天然的尺度:投资回报率(return oninvestment,ROI)。而困扰公益机构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没有一个可以将不同的公益效果进行测算和比较的天然尺度。
比如,举个环保方面的例子,是应该把钱放在建设生态厕所上还是用于治理雾霾?在教育方面,是应该把钱用来资助在广大农村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还是帮助贫困地区的学生改善饮食标准,是捐建乡村小学图书室还是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脑瘫儿童轮椅?罗宾汉基金会的评估方法RM,就是找到了一个类似“投资回报率”的指标,即公益回报与投资成本之比。这种测量公益效果的方法让不同公益项目之间的比较不仅变得可行而且清晰有据。
RM的核心思想是将不可类比的公益回报货币化。这种方法最独特的贡献是将货币价值赋予公益效果,从而将对公益效果的评价转化为对其货币价值的比较。不管你是捐助者、非营利机构、政府官员、立法部门、政策专家或者任何从事公益项目的人,这种方法都可以提供一种可靠、透明的答案。
每年,大约有5%-10%的公益机构在第二年得不到罗宾汉基金会的资助。并不是因为这些机构做的事情不重要、不伟大,并不是说他们爱心不够多,而是因为这些项目没有达到预期设计的目标。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做法和慈善的本质背道而驰,而且非常残忍。但是对捐资人来说,这是最有效率的公益,是最公平的做法,是社会效益最大化的选择。
在商学院,每当我讲完保罗的故事,课堂里都非常安静。我想那些志在投身中国公益事业的同学们已经明白,他们心中的问题不再是是否去做,而是如何将每一个项目的评估公式化和数量化。毫无疑问,这个做法确实是有难度,但不是不可为。我坚信用商业模式做公益,一定是中国公益事业未来的方向。如果这套创新的理念和方法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国的公益事业就不算成熟和理性。
让受助者独立
在《洛克菲勒传》中,洛克菲勒说过一句话让我深受震动:如果不能让受益者独立,慈善是有害的(Charity is injurious unless it helps the recipient to become independent of it)。这个理念,对投身公益事业的人士来说,应该贯穿公益行动的始终。
也就是说,金钱的额度和爱心的真诚固然令人尊敬,但是我们救助受助者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他们独立起来,不再需要我们的帮助,这才是公益最大的成功。如果救助者离开我们的帮助还不能独立,这样的公益不仅有害,对救助者来说,也是一种失败。
斯坦福发展中经济体创新研究院(The Stanford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Economies,简称SEED)的做法就与众不同,他们通过创新的方式来做公益,让受助者变得独立。实际上,创新不应该是企业竞争的专利,社会组织也应该通过创新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去年6月在非洲加纳,30多位当地的创业者接受了SEED的培训。他们的企业规模在15万美元左右,但仍有增长的潜力。这些培训旨在帮助当地企业家战胜非常迫切的挑战,比如如何吸引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学习的内容包括硅谷的热门课程:设计思维、供应链管理等等。培训的讲师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校友和志愿者。讲师们和企业家一道展开工作,帮助他们获得融资,甚至细致到招募合适的团队。这些企业慢慢地越做越好,变得更具竞争力之后,企业家可以去扶植当地其他的缺乏经验的创业者。
SEED的想法是,在与贫困斗争的过程中,增加就业机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私人企业在创造和扩大就业这方面扮演了非常高效的角色。通过孵化创业企业、帮助有一定规模的当地企业更具规模,可以让更多的人摆脱贫困,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位于美国硅谷的斯坦福大学,一直被视为新创企业的孵化器,对硅谷的兴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将这方面的经验运用于全球贫困落后地区的私人企业,就显得格外有意义。真正的社会公益不应该是简简单单地投一笔钱,而应该通过搭建一个平台、形成一个机制,以最少的投入实现最大的效益。有趣的是,SEED的赞助人、斯坦福校友罗伯特·金是百度的早期投资人,这笔投资给他带来丰厚的回报。
让爱心归爱心,让公益归公益,让效率成为最大的公平。要真正做到和西方一样成熟,中国的公益事业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让我们从起点开始。
*文章来源:年代智库
最新新闻
更多